|
尚未完成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
数字人文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以史学研究为例的话,数字人文的一些研究项目正是建立在史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之上的。以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领导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为例,收录数据时就利用了大量学界的既有成果,例如前辈学者对各类古代官员资料的系统整理和考证,方便学者利用。

但伴随数字人文在国内的日益热门,也有不少学者提出疑问。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数字标准化、计算语言学、GIS、HGIS,这些国内已经有学者做了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提“数字人文”?这个专门的提法有什么意义吗?能带来什么新鲜的内容?尤其是对于一向走在“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前沿的图书馆学及情报学,本身就是基于计算的“计算语言学”和已经大量使用数据的量化历史研究,强调“数字人文”似乎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综合这几年看到的国内外已发表的相关讨论或者会议上的交流情况,笔者的思考是,“数字人文”强调的是面对尚未完成的数字革命中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其面对的是未来的知识体系及方法的建构,其回应的是大数据时代基于学者导向(research oriented)的研究需求与基于资源共享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cyberinfrastructure),其建设的是面向数字出生(born digital)的新生代人类的认知方式系统与路径。使用“数字人文”这个术语不是为了改头换面来强行圈地,而是一种处于更大愿景下的策略考虑,是顺应数字时代而生的。
正如金观涛教授在《数位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中提到的:“因数位技术在大量文本分析中的地位直接和判定知识真实性有关,故它在人文研究中将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更具中心位置。随着适应于各类人文研究(如语言学、历史、文学、传播、民间文化等)不同研究需要的各类专业电脑数据库的建立,以及使用IT技术对文本深度挖掘技术的发展,将会出现一门称之为数位人文学的新学科。”(见项洁编:《数位人文研究与技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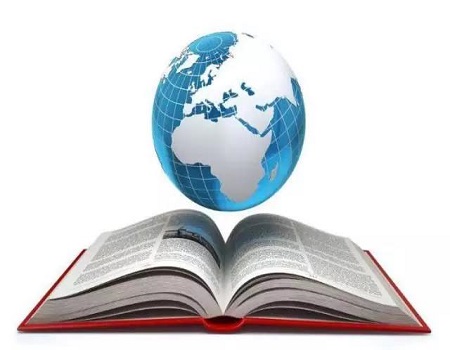
数字人文所带来的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一点是,从“基础数据”的层面,实现真正的跨学科协同合作,并从方法和路径的层面打通自然科学、应用工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艺术的综合研究,也使得研究者从自身的学科立场出发,得以扩展到其他领域,并能以“问题导向”出发,与其他学者协同研究,实现研究层面的资源最大共享化、分析方法的最大通约化和知识内容的最大综合性。
然而,数字人文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倡导之余也要警惕过分乐观。就目前而言,数据的获取和开放程度是中国数字人文面临的一大挑战。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例,已经数字化材料的获得远远不是开放的。各类古籍数据库多如牛毛,但数据共享的做法仍然非常罕见——许多数据库都以商业模式运营,必须得到学术机构和研究者的订购,才能生存。因此,它们的数据开放程度肯定是有限的,这对不同电子资源之间的协作造成一定障碍。

与此相比较,基于互联网的社群讨论和传播,却显得更为融洽、富有活力。许多关于数字人文的学术交流和讨论已经通过非传统的渠道进行,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例如,不少相关的学术动态是在微信号和群组上发布与传播的。与此同时,推动数字人文的发展,还需要更多注重研究的实践,例如培养研究者制作可视化的技能,或传授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操作、解读等技能。随着各种数位学术资源变得盛行,数据库的使用越来越重要,对研究者的培养也理应加入关于这些工具的内容,让学生们对它们的特点和优劣有系统的了解。面对充斥着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可视化图像,我们需要带着什么意识去解读与提问?学者在自己制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诚然,不是每一位人文学者都要系统地学习数据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但不管是否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都值得所有文科学者接触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系统的反思。人文社科学生的培养如何应对数位人文带来的新典范,也成为学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作者简介: 徐力恒,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陈静,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572期第5版
【本文责编:孟令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