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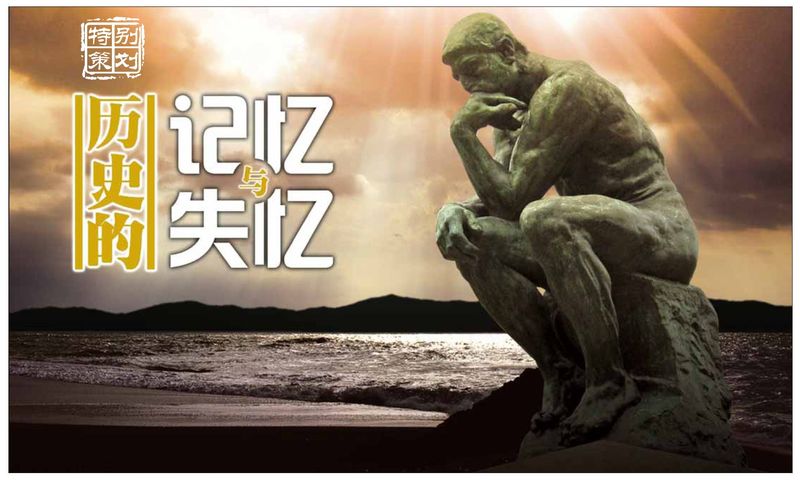

记忆、价值与史学
□本报记者 童力
据说,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叙述是回忆的同义语。只有进入回忆的东西才成其为历史,只有变化的东西才进入回忆。
这段颇为拗口的话表明,历史与记忆、叙述天然地结合在一起。
假如人类失去记忆,叙述就无从谈起,历史就会中断。
两千多年前,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曾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全书写成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之前,孔夫子发出这样的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在司马迁心目中,他有一个使命,即传承历史记忆。而杞国和宋国,在孔子看来,由于他们没有将历史记忆传承下来,因此造成了历史的中断。
恩格斯提供了另一个因失忆而导致历史中断的例子。古希腊的阿提卡,部落、胞族、氏族的集团划分非常细密,然而这是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发生的原因何在,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因为“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历史储存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历史学将人类的记忆记载下来,叙述开来,传承下去。假如历史学不传承、叙述记忆,历史学就不能成立。“记”与“忆”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
一部二十四史,正是储存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大仓库。许多民族没有这样的仓库,所以历史中断了、文明断流了。
我们走过,我们回忆,我们记述,我们前进。历史与记忆,相互交融,不可分割。
记忆与失忆相生相伴
“文学家、埃及学家、史学家、传媒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研究回忆和记忆现象,至今已足足20年有余了。”
这是德国汉诺威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哈拉尔德·韦尔策在2001年写下的一段话。它表明,记忆虽然与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但对它的专门研究,还非常短暂。而且,记忆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的特点,是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
2009年12月,在南开大学,一场学术研讨会正在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历史的记忆与失忆——价值选择与史学功能。
这场以“第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冠名的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它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次专门就历史记忆问题进行研讨。
研讨的目的,已经不限于揭示历史记忆的价值和意义。换言之,历史记忆多么重要、多么必要之类的话,早已是无须多说的老生常谈。学者们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有些东西被记住了,而有些东西却被遗忘了?这里面是否反映了人们的某种价值选择?它对历史学的功能又意味着什么?
哲学家培根说过,人的精神总是天生地倾向于记住肯定的东西和忘记否定的东西。
是的,谁不喜欢宣扬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业绩,而热衷于谈论“走麦城”呢?好汉武松常挂在嘴边的也是景阳冈上如何打老虎,而非其他。喜欢与不喜欢之间,隐约闪动着记忆与失忆、突出与隐没的主观牵引。
于是,学者们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给“记忆”划出类别,指明其中套路。结果,读者便在学者们笔下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记忆样态:个人记忆与集团记忆,文化回忆与沟通回忆,有意识的回忆与无意识的回忆,精神创伤式回忆与日常回忆,解释性回忆与创造性回忆,否定性回忆与代际回忆,等等。
不论哪种情况,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记忆与失忆总是相生相伴,如影随行。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3月02日(第67期)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