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译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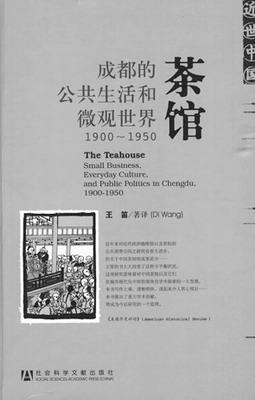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王笛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59.00元
我至今清楚记得1991年春天赴美时,从飞机上看着下面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没有远行的喜悦,只有离别故土的心酸,因为我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到她的怀抱。快20年了,成都仍然是我梦魂萦绕的地方。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好像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即使远隔万里,我生活之大部分,仍然与她密切相关,因为我每天都在研究她,探索她的一切秘密。从《街头文化》,到这本《茶馆》,加之我目前正撰写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公共生活,这三本书可以算是城市微观史和成都叙事的“三部曲”吧。这里主要谈谈我撰写《茶馆》一书的一些思考。
为民众写史
成都人坐茶馆的习惯可以说是名声在外。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机构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没有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如果我们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将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
从1997年我撰写第一篇关于茶馆的文章算起,到今年《茶馆》一书的中文本出版,其间十三四年,可以说是我学术转变最关键的时期,即由研究精英到民众、由宏观到微观。在中国历史学界,还是英雄史观、宏大叙事居统治地位,所以一位前辈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的告诫,引起不少同行的共鸣,他们相信重大选题才有研究的意义,才可能成就好的历史学家。但我怀疑是否真有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热衷于“重大题材”的史家,把芸芸众生视为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不屑于观察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国家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可以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文化有意义的内涵。
我把为民众写史的史观,融汇在我的历史重构和叙事中。这本关于茶馆的长篇叙事,以1900年第一天清早的早茶为开端,在194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堂倌关门而结束。我在“尾声”一节写到:茶馆送走最后一位顾客,辛劳了一天的堂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无论是昨晚最后离开茶馆的茶客,以及正在做梦的堂倌,他们不会知道,隔了五十多年后,一位在成都出生长大但流落他乡的历史学者,会给他们撰写历史。他们不会想到,在这位小同乡的眼中,他们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他们所光顾的茶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坐茶馆的生活习惯,竟一直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较量的“战场”。他们每天到茶馆吃茶,竟然就是他们拿起“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弱者的反抗”。
详描细节,凸显主题
讲述在茶馆里发生的故事,揭示了茶馆的许多细节,这些细节,是我论证人们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如何控制和影响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国家文化等更宏大问题的思考所或不可缺的。引子和尾声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是对半个世纪成都社会和茶馆变迁的概括,有的细节是根据历史记载的一种逻辑重构,如果读者读完本书,再对照我在《街头文化》中对成都的描述,就会发现这种逻辑重构完全是有历史依据的。
日常的研究取向,容易使我们陷入杂乱的细节而难以自拔,这也引起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细碎化的担忧。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这本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个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那么《茶馆》这本书,是靠什么支撑的呢?这个结构就是本书的中心论点: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现代化和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势头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
微观历史的取向,使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城市和城市生活。写城市的微观世界,需要把各种支离破碎的细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历史叙事。我试图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把这个城市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以电影镜头和文学描述的手法展示出来。我觉得写历史有时候就像拍电影,作者的笔触所处犹如镜头,可以用远景、中景、近景,甚至特写,以使读者在阅读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5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