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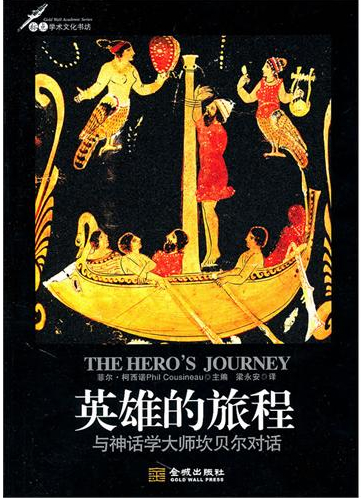
《英雄的旅程:与神话学大师坎贝尔对话》,[美] 柯西诺 (Phil Cousineau)主编,梁永安译,金城出版社 2011年版
激情这东西让大部分精神科医师都忐忑不安。“你对约瑟夫•坎贝尔的崇拜,似乎是你渴望一个弥撒亚的移情作用。”一个朋友得知我想为坎贝尔拍一部纪录片的时候这样说,他是个著名的心理分析医师。我一直希望可以把坎贝尔的精彩思想用影像记录下来,在电影院和电视上放映,留为永远的纪念。我的这个梦想,终于落实为片长一小时的《英雄的旅程》,在1987年首映。这部电影,也来自于各位手上的这本书的内容。
大部分美国中西部的长老派教徒,对于任何的狂热都怀有戒心(运动和宗教方面的狂热除外),我年迈的双亲自不例外。如果我能够把“坎贝尔热”转移为对教会的支持或对医疗事业和经济保障的促进,他们肯定会开心得多。
由于不听师长父母之言是不明智和无礼的,所以在与坎贝尔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岁月中,我都努力克制,不把他当成一个崇拜的对象,而我也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一些好友看来,我并未沦为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仍然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感受能力。
然而,回顾多年来与坎贝尔的相处,我的感受却很像是爱——不单是对他的爱,也是对其他受过他感染的人的爱。看到他们从坎贝尔那里获得的喜乐与成长,是我会花十年以上的努力去为坎贝尔拍一部纪录片的一大动力。我相信,我拍的这部纪录片,将可以让更多人从他那里获得启示。当然,我的这个信念,是源自于亲身经历。
他们认为成群结队地前进是不体面的。所以,他们每个都会从自己选择的地点进入森林——最黑且没有路的地点。如果有路,就一定是别人走过的路,这就意味着你不是在冒险。
——坎贝尔
1972年,也就是三十九岁那一年,我利用教授休假的机会,想完成一项有关谋杀的研究。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的那段期间,我发现早期谈到暴力的文献,都是神话性质的,而让我惊讶的是,见于古代神话里的家庭暴力模式,竟和美国当代的家庭暴力模式出奇的相似。于是我开始读坎贝尔的四册《神的面具》(MasksofGod)。读完以后,我才了解到,坎贝尔对于人类的象征、心理学、灵性和艺术遗产,具有惊人的融会能力,这种能力,是自达尔文以来任何试图了解人的生物模式的科学家必备的。另外,在阅读这几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受益的,并不只是知性方面。读完它们以后,我感到我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观感都迥异于从前。我变得能将自己融入世界之中。因此,我自然会想知道更多坎贝尔的见解,而且也跟很多其他读过他的书的人一样,对坎贝尔其人感到好奇。他的书读得愈多,我就愈有一种冲动,要把他广博的知识与融会世界神话的能力引介给学术界以外的广大听众。
由于我不是个制作电视节目的专家,所以就找来已故的史帕林(GregSparlin)当拍档。起初,坎贝尔拒绝了我们把他的作品搬上电视的构想,因为他认为,最适合表现他思想的媒体是文字。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努力才说服他。不过,一旦他作出了投入的承诺,我就很有把握,我们的影片将可以让人恰如其分地领略到坎贝尔的学术深度与活力,并因此体验到灵魂的深化。虽然当时相信这个信念的人寥寥无几,但我根本就不在意。
就像很多原创性的计划一样,刚开始我犯了很多错,拍摄计划一直止步不前。到了1981年年终,我愈来愈为坎贝尔的健康担心,因为仅仅六个月内,他就得了两次严重的肺炎。虽然他看来康复情况良好,而且健谈如昔,但有医师背景的我还是忧心忡忡。坎贝尔已经年近八十,但却仍然没有有关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的足够多的影像记录。没错,他已经出版了很多本上乘作品,但我仍然强烈感觉到有把他的思想拍成电影的必要,因为正如乔治•卢卡斯(GeorgeLucas)后来所说的,坎贝尔身上具有一种自然流露的“生命力”,可以诱导听众全身心地投入灵性探索之旅。由于感到时间紧迫,我继续加倍努力。
《英雄的旅程》的正式拍摄工作始于1982年,地点是加州大瑟尔(BigSur)的爱斯兰研究所(EsalenInstitute)。在制作人弗里(BillFree)的帮助下,我找来一些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跟坎贝尔进行谈话:从坎贝尔的诗人老友布莱(RobertBly)到诺贝尔奖得主吉耶曼(RogerGuillemin),甚至还有一个以前从未听过坎贝尔名字的年轻女士。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背景不同的对话者可以引发更多不同的话题。我的期望是,众多的话题,加上导演肯纳德(DavidKennard)的技巧,加上爱斯兰研究所的优美环境,再加上坎贝尔多姿多彩的人生故事与生命活力,能让整部纪录片更形象生动。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取材自在爱斯兰研究所拍摄到的对话。
大约四五个月后,当我们开始剪接底片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声音在我耳边萦绕。这是我很不习惯的事,哪怕它要对我说的是:“追随你内心直觉的喜悦(fellowyourbliss)这是坎贝尔很喜欢说的话,本书中将会一再提到。。”我心里的声音反复对我说:“把坎贝尔下一次全国演讲系列拍成录像带吧,因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了。”令人难过的是,被它言中了。
有些人在轻松、不那么正式的环境里表现得最好。因此,在我们第一次进行剪接的时候,用了很多在这种场合拍到的底片。然而,愈到后来,我们愈发现,坎贝尔表现得最好的,是那些他能够自己挑选话题的场合,是那些他能够使用历经几十年才琢磨出来的最完美的材料的场合。
在1982至1985年初这里的1985年初疑为1983年初。我和一个摄影小组追随着坎贝尔游遍全美各地,拍摄他最后一次全国讲学之旅。我们在新墨西哥陶斯(Taos)拍了他的讲演《心灵与象征》,在圣大菲(SantaFe)拍了《神话在时间里的转化》,在纽约她太太主持的“大开眼界”剧院(OpenEyeTheater)拍了《永恒的哲学:印度教与佛教》,在旧金山的美术宫剧院拍了《西方之道:亚瑟王传说》和《圣杯的追寻》,在旧金山的加州历史学会拍了《当代的神话:詹姆斯•乔伊斯与托马斯•曼》。就这样,我们得到了长达五十个小时的母带,而坎贝尔最有影响力的一些讲演的影像记录,也可以永远留存下去。自此,我没有再听到某个声音在我耳边回响。
坎贝尔进行全国性讲学期间,每当一场讲演或研讨会结束,总会有人跑来问我们:“这个坎贝尔是什么来历?他是怎样成为现在这个人的?”总之,凡听过他的讲演的人,莫不流露出对其人、其观念的好奇与着迷。他们提出的问题,促成了我们塑造这部电影以及各位手上这本书的最后形式。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CFNEdit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