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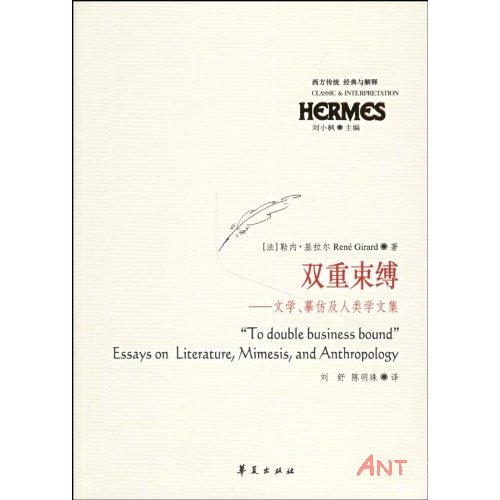
二十多年前念研究生时,我就对人类学这门学科发生了兴趣。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对这门二十世纪春风得意的学科仍然不明究里。
记得当时跑去听讲人类学的课,是在一个很小的教室,学生不到十个。讲者是位从中央民族学院请来的教授,讲“什么是人类学”。起初我想不通:堂堂北大,竟然没人能讲授人类学这门课,却要到外校找人来讲。几堂课听下来,才大致知道什么“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之类,也慢慢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北大没有教人类学的教授。
据那位老师在课堂上说,人类学靠研究“原始宗教”起家——“宗教”在这里是习传生活方式(或习惯)的总称。所谓“原始的”宗教,并非一定就很远古,如今已然不复存在,也可能(实际上更多)指当今还存活着的宗教,因而,其实际含义当指某种尚未达到文明程度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自个儿在心里回忆:什么叫“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依稀记得,“文明”指某种生活方式(或习俗)的典章制度化,从而使得这种生活方式脱离了“原始状态”。据说,如此文明化的发端和演化过程,端赖於这个生活共同体中为数不多的聪明人(我国古代称为“圣人”,《庄子•天下篇》:“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於变化,谓之圣人”=括号内小5宋)——他们一方面“心鹜八极”、一方面明察共同体生活的正反经验,总结出一套秩序设想并诉诸文字。随后,这些文字被这个共同体后来的聪明人奉为经书代代相传,以启示或传统的名义筑起城墙维护起来,所谓文明便由此得以成形(参见尼采,《敌基督者》,第57条)。经过这番回想,再将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举一反三,我才大致明白,人类学研究的是没有形成经书的(因而叫做原初的)生活方式(所以人类学离不开“田野调查”)。既然传统的大学以讲授古典经书的业,北大这样的大学没有人类学教授也就不足为奇了。
课后我找到马林诺夫斯基的书来读,觉得很好玩,但还是不明白他研究这些“原始宗教”究竟要干什么……没过多久,当时在欧洲声名显赫的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人类学就随着结构主义风潮到中国学界来了——据说,法国大学的学生造反运动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兴盛不无关系……古典的文明大书随之被赶出学堂,理由是:任何生活方式都是平等的——有人说,结构主义人类学堪称一场“新的理智运动”(参见巴德考尔,《莱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和社会理论》,尹大贻、赵修义译,复旦大学版1988),看来颇有其道理。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倘若人类学成了大学的基础性学科,人类学岂不就会彻底改变传统教育的基础——学生们无需再念古典的经书,“搞田野”也可以“成人”,那该多好呵。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人类学其实并非仅仅研究所谓“少数族裔”的原始生活方式,也研究古典文明。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不仅有列维-施特劳斯,还有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这位学古典学出身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法国古典学界的当代大师并不少,我们几乎没有翻译过他们的作品,韦尔南的译本却已经起码有了三本(《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三联版1996;《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版2001;《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北京三联版2001)。看来,韦尔南受到我国学界的青睐,并非因为他是研究古代希腊的专家。
韦尔南的古希腊宗教人类学与列维-施特劳斯的原初宗教人类学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双刃利剑,将古典文明从西方传统身上切割下来。韦尔南自己说过:列维-施特劳斯研究的是“未文明化民族的宗教”,后来发展出“无文字民族的宗教比较学”,其方法是:在不同种类的社会现象与话语之间假设一种结构的相似,从而“构成一种完美意义上的社会现象”(《神话与政治之间》,前揭,页88)。在韦尔南看来,这种研究引导列维-施特劳斯从宗教性出发,发现了一种普遍理论的轮廓——该理论把社会看作个体与集体间分为好多层级的交往系统。至于他自己,则是在文明化的古希腊宗教领域做了相同的工作,发展出一种有文字民族的宗教比较学。
与古代的“圣人”之“作”对比起来看,人类学家无异于在重新创造“文明”。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