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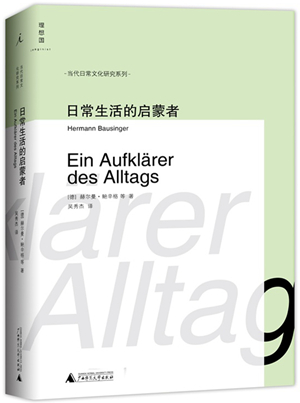
他曾经让灰头土脸的德国民俗学变身为一门现代学科;他在图宾根大学用“经验文化学”替代了“民俗学”,也因此被誉为“经验文化学之父”;他的学术生涯以担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助教为开端,在晚年再度回归到对地方文学史的研究。2016年9月17日,德国民俗学家、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步入90岁高龄,当天他在家乡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举行其新著《施瓦本文学史》首发仪式及朗读会。《斯图加特消息报》文化版编辑Frank Buchmeier采访了鲍辛格教授。
2006年,鲍辛格80寿辰的贺寿之书是对话体的学术传记《日常生活的启蒙者》(中文版,吴秀杰 译,广西师大理想国2014年版),是他的两代学生献给他的礼物;2016年,90岁的鲍辛格给自己、也给他的读者们送上一本篇幅400多页的《施瓦本文学史》(Schwäb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Verlag Klöpfer & Meyer)。
书架已经不堪重负,他早已经不得不把书堆在桌子、椅子和地面上。这些书垛越来越高,高得似乎摇摇欲坠,而他就坐在这书垛之间。这是图宾根大学在鲍辛格荣休之后给他提供的一间办公室,与他曾经任职的研究所不在同一建筑物里面。从窗口仰望出去,他可以看到图宾根的城堡,他一手创办起来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就坐落在城堡的塔楼里。如今,他迎来了90岁生日,一个很好的借口或契机,来回顾和梳理一下他那漫长的学术生涯。
问:鲍辛格先生,图宾根的每一位教授都有权利终身保留一间办公室吗?
答:按说没有。最多是惯例如此,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研究所。我是被非常善待的,能在这里安于一隅。我也尽量不打扰任何人,在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我参与学术研究。
问:您怎么受得了这间屋子里这么混乱的状况?
答:我是从纸质书时代过来的人,那时没有云储存。不过我也承认,有时候我也记不清东西都放在哪里了。几年前我已经把满满一拖斗书交给了古旧书店,以为那些都是我再也不会用到的书。不过,我还是经常怀念那些书,这可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问:自从您1992年荣休以后,经验文化研究发展得怎么样?
答:研究范围扩展得宽多了,也有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国际项目。有时候我有点儿忧虑那些以地方文化为对象的研究方向,因为做覆盖面大的项目比较容易拿到资助。
问:来自外部的逼迫增多了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大学里工作仍然有很多自由,但是人们也能感觉到,文牍管理式的控制妄想症也已经波及学术机构了。有时候,再小的事情都得填写一式三份的表格。要想让项目资助持续下去,必须不断地提交冗长的报告。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阻碍了学术研究。
看民众嘴上说什么
问:让我们回头看一下美好的旧时代:差不多七十年前,作为大学生的鲍辛格是怎样经历了艾伯哈特·卡尔大学(图宾根大学)的呢?
答:我当时注册了德语、英语和历史学三个专业。决定我后来学术道路的文化科学,一开始无非是古代日尔曼语言文学当中一个旁逸斜出的分支而已。那里早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日尔曼文化遗产和中世纪文化遗产都毫不掺假地保存在民众当中——传说、童话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问:您在博士论文里已经对这些思想提出质疑。
答:当时通行的的论点是,口头讲述已经消亡。学者经常把口头讲述与一些幼稚而浪漫的想象连在一起,以为从前人们坐在椴树下的长椅上,在不停地讲述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尼伯龙根的传说》的主人公之一)的故事或者小红帽的童话。我骑着自行车,跑了我家乡周围的地方,去学校和乡村酒馆,去听一听人们到底在讲述什么。我发现人们还是口头讲述很多东西,也有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只是采用了新形式。比如一位大货车司机说,他曾经让一位女搭车人上车了。等到这个女人在副驾驶座位上坐下来后,他就挂不上档了,只好用一档慢腾腾地爬行。等到那女人下车以后,挂档就又好用了。那位司机坚信不疑,那个搭车女是个巫婆。
问:今天可是听不到这类不着边际的故事了。
答:不同意!要是发生了什么难以解释的事情,人们还是倾向于非理性的推测。这些有关魔法的想象是怎样传播开来的,这才有意思。恰好是18世纪那些理性启蒙著作,帮助这些东西传播出去,将迷信说法固定下来,因为一些鬼故事就是因为这些书才为人所知的。这个现象是我在1960年的教授入职学术演讲中讨论的话题。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观察到这类现象:比如某个号称神医的愈疗者,假如媒体对其有负面报道的话,跑去找他/她的人会比没有报道时还多。
问:您如何解释自己年轻时青云直上的学术生涯?
答:有幸运的外部条件。在50年代中期,民俗学研究所有一个助教职位空缺。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师范专业的教学实习阶段,如果当时没有那个助教职位的话,我就可能是一位中学教师了。我以助教的身份实际上掌舵研究所,因为名义上的所长是斯图加特的一位文物保护专家,他只是每星期四过来看一下,其余的事情完全放手不管。1959年我取得了教授任职资格。一年以后,自战后以来一直虚位的民俗学讲席要重新设立,我就被聘任为讲席教授。
问:您接手教授讲席时,还没有学生运动来打破原有的僵化结构——“穿教授礼袍的学究”。当时大学里的氛围如何?
答:人们经常说,德国的大学是从1968年才开始改变的。实际上,早在这之前转变已经发生。在图宾根大学的哲学系,60年代初几乎已经没有人穿教授礼袍了。在我的研究所,教师之间以及年长的大学生之间已经开始用“你”而不是“您”来彼此称呼了。
问:您在课堂上讲漫画和地摊小说。当时的精英学术圈对您热衷于低俗的研究对象这一做法,有什么反应呢?
答:很不一致。一方面我很快就成了全国范围内大受欢迎的学术报告人。同时人们也指望着,我的专业领域的任务是留住老东西。民俗学是遗留物研究;现代化带来的影响,交给其他学科来研究好了。在当时,我是有意识地将这个学科扳上了另外的轨道,因为在技术世界里当然也存在着民间文化(鲍辛格在1961年出版了《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中文版,户晓辉 译,广西师大理想国 2014)。我想把研究扩展到更宽泛的领域。对我来说,迈向并探索新领域的吸引力更大,我不太愿意留在在一个已经被透彻地研究过的领域中,做破解该领域最后一个谜团的人。我要让民间文化穿越高端的学术领域,再通往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斯图加特消息报》文化版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