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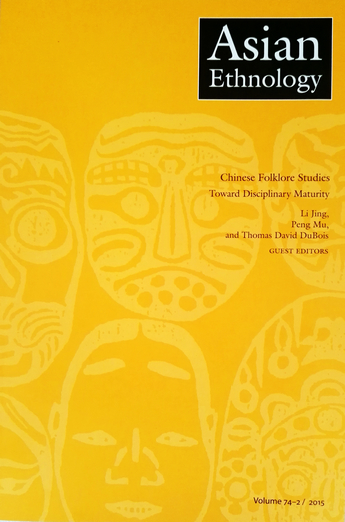
2015年11月,名为“中国民俗研究”(Chinese Folklore Studies)的《亚洲民族学》(Asian Ethnology)特刊(第74卷第2期)在日本名古屋出版。经过五年的努力,在国内外学者的精诚合作下,由李靖、彭牧和杜博思(Thomas David DuBois)担任特约编辑的特刊终于付梓发行。
《亚洲民族学》的创刊可追溯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1940年,北平辅仁大学在叶德礼(Matthias Eder)及其他汉学家的努力下,成立了人类学博物馆。1942年,博物馆的下属期刊《民俗学志》(Folklore Studies,或译《民俗研究》)创刊。此后,在叶德礼等外籍教职员以及国内学者赵卫邦等的参与下,该学刊坚持每年一期,用英、法、德语介绍东亚国家的民俗研究情况,包括东亚地区田野调查的最新资料、理论与方法论的进展等。1948年,该刊迁至日本,1963年改名为《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 Studies)。直到2008年,因“民俗”(folklore)一词的局限性,该刊改名为《亚洲民族学》(Asian Ethnology),目前由日本南山(Nanzan)宗教与文化研究所以英文出版。作为“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收录的民俗学国际核心期刊,该刊在亚洲民俗学研究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特色之一是鼓励亚洲本土学者的研究。
《亚洲民族学》创刊以来,除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赵卫邦在此发表了整体介绍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论文以外,后来虽然零星有中国学者发表中国民俗研究的文章,但整体看来,呈现出来的大多较为碎片化,缺乏综合全面的展示。而本期特刊,由六篇中国学者的文章组成,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中国民俗学兴起的历史、近年的发展轨迹与当下研究的现状。
李靖作为特刊的特邀编辑,其《中国民俗研究:走向学科成熟》(Chinese Folklore Studies: Toward Disciplinary Maturity)一文,可视为本特刊的绪论。在总结其他五篇文章的基础上,该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本特刊的主旨。作者主要从民俗学史的角度切入,在回顾了中国民俗学发端、早期发展中的社会背景及政治倾向后,又分别从三个方面阐明了新世纪民俗学学科的转向。首先是对“到民间去”(going to the people)的新理解与新实践,如“民”的概念的转变。其次是对当下民俗学者身份的重新评估。作者肯定了学术界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肯定了学者们的自我意识。最后介绍了中国学者与国际民俗学界的交流,特别是在国外理论的引进及应用方面。作者提到,在探讨这期特刊中主要表现什么时,有两个引进的概念一直被学者们提及,它们分别是体知(embodiment)和语境(context)。其他五篇文章,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两个概念,并在实践中对它们进行了反思与推进。正是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俗学正在逐渐走向学科成熟。
安德明与杨利慧合作撰写的《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Chinese Folklore Since the Late 1970s: Achievement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细数了中国民俗学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当下三十多年的发展情况,展现了民俗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中的浮沉命运。该文第一部分为民俗学的复兴与重建。这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地位及机构设置,还特别提到了为民俗学学科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钟敬文、张紫晨等老一辈民俗学者。第二部分为理论与方法论的新拓展。民俗学逐渐恢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主要实现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三个方面的转变,其间还涉及到国外理论的译介与应用。第三部分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是中国民俗学界三十多年来在社会文化工作中影响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件事。第四部分为困境与挑战。作者就学科定位、个案与区域研究等方面的问题表达了对民俗学学科前景的思考。
刘铁梁的《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例》(Village Production and the Self Identific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一文,提出了中国村落研究的新视角。作者通过对房山农村地区的持续观察,回归生活本身,看到了村落在工业化影响下产生的“劳作模式”(village Production)的变迁。而村落劳作模式(territorial village production)包含着村民们在特定的生产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身体经验与感性知识,正是这种共享的身体实践,构筑起了村民们的自我认同及其村落共同体。作者以京郊房山沿村的编筐业为例,从历史文献到口述资料,梳理了该地区的城乡经济结构的变化,并详细说明了该项手工业对该地区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村落的集体信仰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作者进一步肯定了劳作模式对村落认同的积极建构作用。
陈志勤的《为了谁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的主体置换与地方文化的再生产》(For Whom to Conser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Dislocated Agency of Folk Belief Practitioner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ocal Culture)一文,可以说是对国内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质疑与反思,特别是在民间信仰方面。作者在浙江省绍兴市调查时,发现其大禹信仰与舜王信仰分别被置换为名为“大禹祭典”和“舜王庙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的置换,不仅是名称上的,更是主体上的。再加上之前旅游业的发展,该地的信仰文化不断被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因利益等因素,原来的信仰主体为政府所代替,连带着其信仰文化也被重构,而该信仰的真正主体即当地民众,却丧失了对自己的文化资源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权力,甚至面临离开家园、放弃记忆的困境。基于这些事实,作者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问题:为了谁而保护。这种“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值得深思的。
彭牧的《不可见的与可见的:与阴间沟通》(The Invisible and the Visible : Communicating with the Yin World)一文,创造性地用实践理论来探讨一个村落的信仰问题。作者从湖南茶陵地区村民们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出发,解释了当地人如何在缺少制度性宗教的条件下形成有关阴间的概念与信仰。作者参与观察了该地区阴历七月的鬼节(中元节),结合自己的体知,细致描述了村民们在祭祀期间的各种活动,如“下饭”、“烧包”等。另外,作者还特别提到了当地的两种灵媒,一种是业余的,即“颠祖牌”时被祖先附身的普通村民,另一种则是专业的,即“梅爷”,可“查家”、“调魂”等。“梅爷”的存在,以村民们共享的关于阴间的知识为基础,而这又反过来又促进了村民们对阴间的信仰。正是这些“实践的信仰”(practical belief),使村民们在传统实践的“做”中完成了对阴间的想象与确认,并使之代代相传。
杨利慧的《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神话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反思》(The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of “Context”: Reflections Based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of Myth Traditions)一文,是对学术界“语境”(context)一词泛滥应用的质疑。作者立足于河南淮阳、重庆市走马镇司鼓村、山西省洪洞县侯村等三个社区的田野调查,提出了对“语境”这一概念之有效性的反思。语境虽然影响着神话文本的构成和变化、神话的讲述场合、讲述者与听众的构成与规模以及神话的功能与意义,但这种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限度表现在神话的核心母题、母题链的组合与类型、基本情节等方面的稳定性。基于对“语境中的民俗”的反思,作者提出结合文本与语境、历史与具体表演时刻(the very moment)、区域与比较、集体传承与个人创造力的“综合研究法”(synthetic approach)。
本期特刊,突显了中国学者在民俗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探索与进取之心。这组文章不仅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民俗学界最新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让中国民俗学在国际民俗学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打开一个了解领略中国当代民俗学学科成熟的窗口,也必定会进一步促进国内外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相信,不管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民俗学界来说,这都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作者信息:沈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本文刊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