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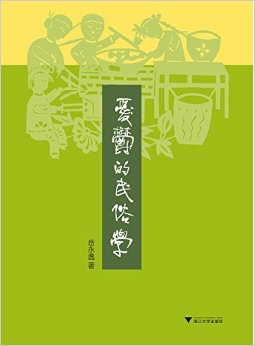
《忧郁的民俗学》岳永逸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38.00元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映。
长期研究民俗的岳永逸在《忧郁的民俗学》中主要写了民俗学科的红火、老母的暮年、小我的悲喜、艺术的光晕、民间的段子、乡土的音声、节庆的盛大、泰斗的脾气、诗人的才情等。对于民俗学科的兴盛,作者理性拨开表面浮华,指出现在的民俗学乃至民俗本身存在两大隐忧,即被体制化和被商业化的风险。
被体制化的现象很多,比如一些传统民俗(如“走阴”)被简单地归入迷信被打倒。被商业化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民俗本更倾向于“小我”的内心表达,其“演出”场所往往是“地当舞台天当幕”的露天,现实中却被推上霓虹灯烘托的剧场舞台,就此着重举了两个典型例证:相声和二人转。这种经改造的民俗早就脱去了民俗形态的本原,内容被曲意顺从了商业的最大化。
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到了母亲的病。就医学病理而言,母亲患的是抑郁症。不过,作者从民俗角度着重剖析了“病因”。这位长期生活在川北、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来到儿子所居的京城后,由于长期与乡土的隔离,也因为儿女长期在外各种习惯的差异,母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这样的体会并不新鲜。记得笔者每次回老家农村,常听一些老人念叨,称不愿意在城里的儿女家呆太长时间,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坐牢”。这种“牢”并非形式上的,而是覆盖到起居、饮食、出行等各个角落的文化区别。许多乡邻辛辛苦苦把儿女培养成人,儿女最终如已所愿跳出“农门”。然而,乡邻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像先前想象的那样到城里享福:有的受不了城乡文化的差异,最终还是回到农村;有的“委曲求全”屈居于儿女门庭之下,却郁郁寡欢;有的在长期不适应中,导致家庭矛盾频频……在乡邻眼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乡间民俗就是他们精神领域的“根”,这条“根”不可能从物质层面轻易改变。没有这条“根”,他们的生命便失去了色彩,就像一个人顿时失去了呼吸功能,如同该书作者的母亲,久而久之便落下了精神“病根”。
民俗其实是一种基于环境、社会等形成的文化习惯。对于民俗,我们经历了鄙夷到正视再到推崇三个阶段。鄙夷是因为闭关锁国之时,急于强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破除旧传统旧习俗,努力向西方学习,中国才可能走上自强自立之路。改革开放后,民俗现象作为一门学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而今天,几乎每个地方的旅游景点,都有地域性的民俗展览。
对于民俗眼下的这些繁荣,作者显然并未欣喜,反倒觉得,这种推崇带着浓郁的体制与商业气息。除了前面提到的相声和二人转,春晚是民俗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话题。近年来,将春晚比作民俗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不过作者并不这么看。春晚有几十年的传统这是事实,但众所周知,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自下而上的自觉,相反是因为体制综合各种资源的结果。从内容上看,春晚每年花上近半年时间大张旗鼓地准备,看似精益求精,实则磨去了各种艺术原本最具民俗的特色棱角。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映。这种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众的想法,比如良好的愿望。民俗虽然无法剥离传统因素,但民俗并非一成不变,有的会同地域文化结合,有的则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改造。
其实,民俗也并非“大雅”,难避局限性。如就作者一再推崇的农村戏剧形态,许多戏剧只要稍加琢磨不难发现,其内容不乏苦读诗书进京赶考、向体制靠拢的强烈渴望。而被作者大书特书、玄乎其玄的民间“走阴”,科学性真实性也颇存疑问。当然,流传于乡村的许多民俗并没有刻意遵循科学,他们看重的是一种话语权、一种源自个人本体内在欲望的外在表达。从这层意义上看,民俗也是一种呐喊。
○王磊(书评人)
文章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4年09月17日 14:19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