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圣性的衰减与存留
书乡周刊:我们读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会感觉所谓“神性”多存在于边远、偏僻、受现代性冲击较小的地方,像今天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过渡成了“人性”的世俗空间。如您做的研究,所谓“神性的北京”也很大一部分得在史料中去复原了。是不是说,依托乡土成长的“神性”,天生是和都市有矛盾的?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去神化”是一种必然吗?
岳永逸: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有两种声调,一种是神离人越来越远,神圣性的衰减是总体趋势,不管是基督教的上帝、耶稣,还是伊斯兰的真主、佛教的佛祖,都被减轻了对人的完全支配,而给予个体人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神并没有离人越来越远,因为现在是风险社会、信息社会,人们生命中面临更多的不可把控和偶然性,因此会主动去靠神来解决,所以其中也有一个神圣性的递增。这两个语调相互不能说服。
但都市文明的确一直在消减神圣性。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农耕文明的时代,而从清末开始按照西方人的知识标准来进行城市改造,包括交通、人居等,把城市弄得和乡村越来越不一样,所谓“城乡差别”就是在这两百年里形成的。过去的官员退休后会告老还乡,在那时人看来,在乡下生活和在京城生活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但今天没人告老还乡了,城市像巨大的磁铁一样,把人往里面吸附。上世纪40年代北京大街小巷对“胡黄白柳”四大门的信仰,和现在的乡村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后来随着医生、警察等现代体系的建立,把接生婆、巫医、香头、阴阳师等传统的有一定职业功能的群体往外赶。这是制度层面上的,但从另一个层面说,生活在城市里若干人等,又会在个体层面上,用自己的形式把神请回来,所以很难说,要看从哪种层面上讲。
书乡周刊:所以民间民俗宗教以后的存在发展,更多会是依托个体形式了?
岳永逸: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春草秋虫一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存在可能,有很强的伸缩性和变形能力,而不是像顾颉刚那一辈知识分子一样,认定它们肯定会消失。今天的老乡受教育程度比原先高很多,乡村基本建设比较完善,但这一二十年,从前用来庙产兴学的庙又恢复成庙宇。只能说,如果有外界力量想让它消失,肯定会遇到巨大的挑战。
书乡周刊:其他国家对民俗宗教的态度和做法,有没有可以借鉴之处?
岳永逸:其实是政治命名术的博弈过程。比如印度教是多神崇拜,但没有被视为迷信,当时的英国政府也没有对其进行污名化,现在它在东南亚很多地方还能大行其道。而日本是另外的例子,明治维新时也有很多破除民间迷信的举措,但与此同时,又把围绕神宫、神社的一系列祭拜命名为神道教,并提升到国教的地位。虽有基督教西方宗教等进入日本,但并没有把它原来的本土宗教信仰予以妖魔化。现在到日本去旅游,许多著名景点就是这些神宫神社。
而中国情况比较复杂,在列强入侵、救亡图存的语境下,改变积贫积弱国情的心态太迫切,所以精英们把落后挨打的原因归之于此,上归“孔家店”,下归民间信仰,到现在就有些尴尬,一边要申请“非遗”,一边要破除迷信。也有一种归类的办法,即把民间信仰中的一些归到佛教,另一些归到道教,但这也不对,因为比如老百姓说的观音,和僧人说的、道士说的观音是不一样的,它是完全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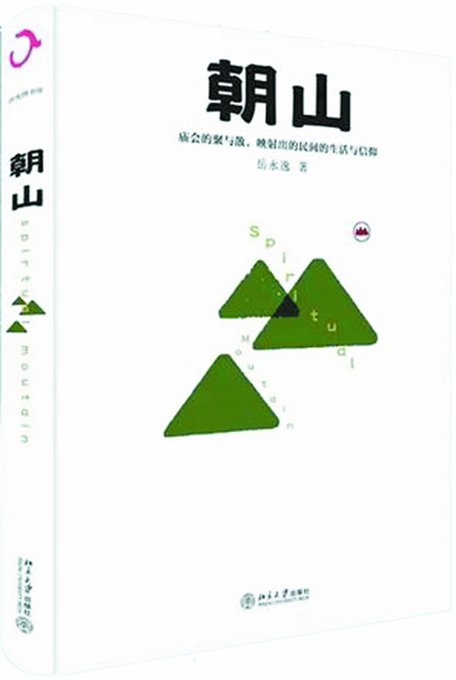
人物名片

岳永逸,民俗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出版《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朝山》等多部民俗学专著。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2017年7月7日 TF003版
【本文责编:张倩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