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2月20日 09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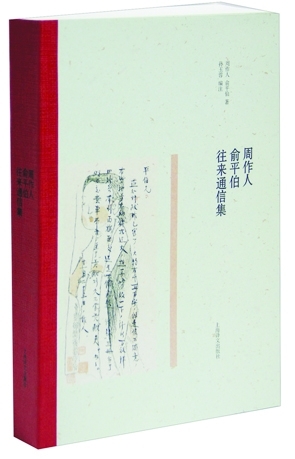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周作人、俞平伯著,孙玉蓉编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58.00元
由俞平伯研究专家孙玉蓉编注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收二人书信391通,历时四十余载,内容丰富,掌故繁多,且装帧精美,彩色图版尤其喜人。现代文学史上有些不常被提起,却意味深远的往事,可从这些信中读到,因补充了不少细节,遂使轮廓清晰起来。此处拈出几件,略加述说,以飨同好。其中,延续时间最长,本书提供材料较多的两件,即关于日本的杨妃传说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孙玉蓉已在《编后记》中详细介绍,但因重要且有趣,下面仍作一简要复述。
日本的杨妃传说
1929年2月俞平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后收入他的《杂拌儿之二》),认为细读唐时的歌和传,发现用词模糊狡狯,似暗示杨贵妃并未真死于马嵬坡,仅“使牵之而去”,末了“忽闻海上有仙山”,隐写杨妃已流落女道士家。后周作人听日本友人说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遂于1930年7月30日致信俞平伯,告以传说详情,还寄了四帧照片,以供参考。俞兴趣大增,于8月1日复信探讨。周又于8月6日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信后来都发表了。过了三十余年,周作人从竹内好所编日文杂志中读到在日本尚有杨贵妃后代子孙的新闻,据云还有古时文件展出为证,马上告诉了同在北京的俞平伯。俞1963年11月17日的信就是与乃师谈这件事的。周读俞信后,触发灵感,当即写下《杨贵妃的子孙》一文(刊当年12月21日香港《新晚报》,现已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师生间相互关注、切磋学问,对一具体问题探讨整整延续36年(俞最初撰文在1927年11月),堪称学林佳话。
俞平伯的红学研究
早在1921年4月,俞平伯受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启发,开始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时间长达三个多月,信稿订成几大本。此即他后来《红楼梦辨》的雏形,这也是俞一生红学研究的发端。但在周俞通信中,谈及《红楼梦》的信保存得并不多。书中收有1928年3月1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告诉他3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周将自己的杂志给了俞。到1953年末,作家出版社出了校订版《红楼梦》,周作人读后发现问题较多,于1954年2月致信俞谈了看法(此信已佚),俞即于2月28日回信,谈到整理者系“湖畔诗人汪静之,渠对北地言语风俗毫不了解”;而对作者生卒年及族籍等采用周汝昌说,也认为不对;并预告第二天《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将有自己与王佩璋写的相关文章发表,盼周留意。同年3月22日他又给周去信,汇报自己从事《红楼梦》研究的近况。孰料几个月后,一场全国性的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到1963年8月,《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俞平伯长文《〈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俞的复出和“落实政策”,但文章很快又受到批判。现在,通过幸存的1963年11月17日俞给周的回信可知,此文发表时“已被节去三分之一,故欠贯串,致结尾尤劣……”现在收入《俞平伯全集》的文章也是被删稿,原稿已不复见。如非通过这些信,我们无由得知当时情况。从信中我们也知道了此文稿还曾经周作人事先阅读,并两次写信提出意见。
有关“诗的效用”的争鸣
本书所存俞平伯最初致周作人的信,写于1921年3月1日,俞当时还不知到八道湾如何走。此信中已在谈《新潮》杂志组稿的事。所存第二信系1922年3月2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是讨论“诗的效用”问题的,其实是对俞平伯刚发表在《诗》月刊创刊号上的长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的批评。可见他们师生间深入长久的交往,还是从平等探讨学问开始的。
这篇长文是俞平伯早年论诗的代表作,一万三四千字,当时俞才21岁,文艺观点相当激进。他在文中说:“现在的不能使大多数人享乐艺术,正是大大的缺憾……我们应该去努力打破文字语言底障碍,建设合理的社会制度,促进人生文学底高潮。”又说:“现今的文艺的确是贵族的,但这个事实不但可以改变,而且应当改变……我们应当竭我们所有的力,去破坏特殊阶级底艺术,而建设全人类底艺术。”他提出,文学的作用不是让人“感着美”,而是“使人向着善”,所以诗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感人”,第二个是要“感人向善”,第三个是“所言者浅所感者深”。
作为俞平伯的老师,且是当时文坛上最有影响的批评家,周作人当即撰文提出批评,文载1922年2月26日《晨报副刊》,此即《自己的园地之五·诗的效用》。本书所收第二封信是文章发表第二天写的,周对自己的意见又作了些补充。周在文章中强调:一、“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地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这里的“通事”即翻译,多指口译者,即今之所谓喉舌。二、“善字的意义不定,容易误会”,从来的“劝善书”中“多含着不向善的吃人思想的分子,最容易使人陷到非人的生活里去”。三、艺术价值不能“以能懂的人的多少为标准”,如文学家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此文写于九十多年前,作为文艺理论,自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
当时的俞平伯精力充沛,血气方刚,他的文章同时还受到杨振声、梁实秋的批评,他一一作出回答,在《诗》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与金甫谈诗》答杨振声,在6月2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驳梁实秋,在《诗》第四期上发表了《与启明先生谈诗》——这就是本书所收1922年3月31日平伯的回信(发表稿略有不同,也附书中了)。相比之下,俞对周真是分外小心、恭敬的,虽然仍坚持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不过,俞的这种激进的文学观并没能坚持多久,到第二年,他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野有死麇》与“不求甚解”
在《语丝》周刊第31期(1925年6月15日出刊)中,有一篇《野有死麇之讨论》,署名顾颉刚、胡适、俞平伯。这是对《诗经·召南》中一首著名情歌如何作诠解的学术探讨,在当时很有影响,其中部分信件后被俞平伯收入《杂拌儿》。周作人读《语丝》后,于6月18日致信俞平伯说:“读《野有死麇》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他,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帨解作门帘即犯此病。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的老话,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既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然的了,还怕什么狗叫?这也是求甚解之病。……”我以为,周作人这里的借题发挥,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艺批评原则,那就是反对“故意穿凿”,反对“失却原来浅显之意”。文艺批评者所依循的最基本的东西,就应该是读作品时浑然一体的审美感觉,感觉不够,靠穿凿来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陶渊明之“不求很懂”,其实恰恰是“很懂”文艺规律的得道之言。
“《‘我来自东’》最无聊”
1925年8月1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对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丛刊《我们的六月》中的作品作了一番评点,其中说到:“《‘我来自东’》最无聊,亦可谓读之令人不快,因完全系仿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一流,我觉得凡仿都不佳,因即是假也,现在似乎有这一种倾向,以为仿李杜不可而仿适之、达夫则可,殊可笑。”此话藏在信中,过去不为人知,其实却是石破天惊之语。
《我们的六月》,1925年6月亚东图书馆版,收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叶圣陶、白采等近二十位作者的三十几篇作品,诗、散文、小说均有,而小说最薄弱。《“我来自东”》是一篇写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无聊生活的小说,作者金溟若,本名金志超(1905-1970),当时仅20岁,这可能是他早期试作;几年后,他又在《奔流》、《东方杂志》等处撰文,曾与董每戡合办上海时代书局,译有《世界文化史》。这篇小说的故事和文气像极了郁达夫的《沉沦》,但又平添一层低俗,字里行间满是神经质的抒情调子(这在当时创造社作家中较流行),难怪周作人看了会不舒服。但我们不可忘记,最早对《沉沦》作出肯定,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坛地位的,正是周作人。所以,他后面的结论亟须引起注意,其要害是:五四新文学以反对因袭、反对死文学和老调子起家,现在用今日的白话,打着新文学旗号,却重又走上因袭之路,岂非可怕的事?
事实上,不光文学革命,中国的种种变革,在翻天复地之后,因群体内里的精神实质未变,又悄悄回到原点的事,确实太多了。这是周作人在《代快邮》、《北沟沿通信》等名文中一再说过的,也是他毕生忧惧所在。读周作人信札,正如读钱锺书《管锥编》,奇突的思想扑面而来,只要观者有心,便觉应接不睱,细加咀嚼,则受用不尽。
晚明散文与五四新文学
将晚明散文看作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源流,是周作人一大发明。但这思想何时形成,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本通信集提供了明确的线索。1925年5月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信,说收到周借给他的明人王季重《文饭小品》,“看了数篇,殊喜其文笔峭拔……行文非绝无毛病,然中绝无一俗笔;此明人风姿卓越处”。第二天,周又致俞,说王季重文殊有趣,却还不如张宗子的自然,张宗子《琅嬛文集》比《文饭小品》更佳。后面一段话极重要:“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篇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随园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以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全是一路,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它有一种新气而已。”(此信曾编入《周作人书信》,本书依原函校订,故略有出入)。看来这是周较早谈到这一思想的文字。既称“我常常说”,说明这段时间这已是他的一个放不下的话题。但此处并未特别强调晚明,而是从清代的板桥冬心经明代文人再上推东坡山谷,是整个一条文学史的线索,突出晚明的提法似还在酝酿中。但俞平伯、顾颉刚等这时正传阅《琅嬛文集》《文饭小品》,可见读晚明、谈晚明已是他们圈子中的热门。三个多月后,俞在8月21日信中,将自己一篇短文《梦游》掩去作者名,问周是否近人之作,并说颉刚认为是明人的。结果周与钱玄同都认为是明人之作(见周8月22日回信),这使俞得意非凡。1926年11月,周撰《〈陶庵梦忆〉序》,这是俞平伯标点的明人文集,序中有一段话与前相比又有推进,其中两句尤值得注意:“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另据1928年3月27日周致另一学生江绍原信,周托他代搜三种明人文集,即袁宏道《皇明文隽》、袁中道《珂雪斋集》、袁宗道《白苏斋集》,正好是“公安三袁”,周说自己将“编选明文”(信载《周作人散文全集》卷五)。这也是个重要信号。可见自1925到1928年初春,他这一思想已酝酿成熟。此后,1928年4月28日有周致俞信,也有俞致周信,都谈到周为《杂拌儿》写序跋的事;自这年六七月起,两人又有多信谈到为《燕知草》写序跋事。事实上,周作人关于晚明散文与新文学关系的表述,最早就是在给俞平伯这两本散文所作序跋中完成的。到1932年,周在辅仁大学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演讲,更使这一思想广为人知,造成了当时文坛上下无不谈晚明的风习。这中间,周的又一学生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原拟书名《冰雪小品》,周俞通信中多有提起),也为此一风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4.19蒙难日”
在1929年4月26日,及1930、1931、1932每年4月19日前,甚至到1935年4月20日,周俞之间都有信件,或隐或显提及“4.19蒙难日”,并多次相约聚会吃饭以作纪念,这很令人瞩目。周作人《永日集》中,有一篇《在女子学院被囚记》,将发生在1929年4月19日的事写得很详细。表面看,这是北大内部校舍之争——法学院学生到女子学院抢占校舍,但周作人对这种不讲理、不讲法,公然打人并囚禁教师、学生的事,极为愤慨。他怀疑这背后有国民党背景,所以用了当初《前门遇马队记》的笔调作描写。事后,周又拉沈士远等人与校方交涉,并多次找军政要员商启予等提抗议,事隔几年仍耿耿于怀。虽俞平伯说“做纪念其名,吃饭其实,何乐不为乎?”(见1930年4月9日信)但在周作人,却是半真半假,内心不平之气长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自1927年国民党“清党”并于“4.12”镇压民众后,周与鲁迅一样,从此誓与之不两立。他的《闭户读书论》引起左翼及后人很多误解,其实也是反抗国民党专制的。他从报上看到胡适受国民党上海党部胁迫,不顾先前的不快,翌日(8月30日)即致信奉劝:“‘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他在《永日集》序中也说:“我的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戶读书论》中,兹不赘。”他1929年撰文极少,几近停笔,这是对专制体制的失望和绝望,也是无声的反抗。然而终于还是写了《在女子学院被囚记》,他在文末附记中写道:“近一两年头脑迟钝,做不出文章,这回因了这个激刺,忽有想写之意,希望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写下去,所以我颇对于此文有一种眷念与爱好。”这是说,因被囚一事,他找到了新法,即从眼下具体专制写起,揭出背景(文中多处直指“军政当局”),同时批判专制传统,同样可击中要害。他对此文和此事的重视,正可从这一点上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