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与仪式
作者:[英]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
译者:刘宗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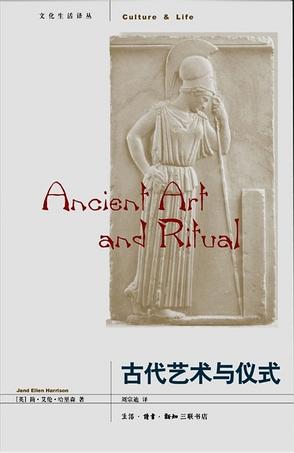
三联书店
2008年9月
文化生活译丛
定价:19.00元
《古代艺术与仪式》译序
刘宗迪
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1850 -1928)是西方古典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界女杰之一,西方大学学术圈中第一位女学者,布卢姆兹伯里文人圈中的活跃人物,意识流写作的创始人、才女沃尔夫对她充满景仰之情,是她晚年亲近的年轻友人之一。
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古典学界,正与其研究的对象一样,古板、沉闷而烦琐,而哈里森的出现,则为这个暮气沉沉的学术殿堂吹进了一股新风。她率先运用现代考古学的发现结合古典文献解释古希腊宗教、艺术和神话,开辟了古典学研究的全新范式,这种“双重证据法”如今早已成为古典学术界的常规做法,但在当时,哈里森的研究却引起了一班一味钻故纸堆的保守学者尤其是她的一些剑桥男同事的剧烈反应,更加之她的女权主义倾向和终生未嫁、不拘小节的生活风格甚至同性恋的嫌疑而授人以柄,因此,她尽管在英国的上流文化圈中名动一时,但终其一生,在她赖以安身立命的古典学术圈中,却一直郁郁不得志,深受剑桥男性同事的排挤和构陷。但是,尽管其学术生涯倍受打压,从她的时代起,她的学说就对包括古典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文学史、戏剧学、考古学等在内的许多重要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她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或曰“神话-仪式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学术界盛行一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界后半叶,随着哈里森那些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新发现广为传播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常识,哈里森的名字反倒逐渐失去光彩而被人遗忘了。那本被视为现代知识渊府的《大英百科全书》,甚至都不肯给哈里森这个曾经名动学界的名字保留哪怕一个简单的词条,哈里森这个曾经让剑桥学堂的男人们极端尴尬的名字,被有计划的抹杀了。不过,风水轮流转, 20世纪后期,当年剑桥学术圈中那些对哈里森横竖看不惯的须眉浊物们早已无人理会,哈里森的名字却凭借着女性主义的风潮和人文学术研究的转型而重新被人记起,这位欧洲学术圈中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学者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哈里森深受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和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金枝》一书的影响,尤其关注对于古希腊艺术和神话的宗教与民俗渊源的探索。她认为所有神话都源于对民俗仪式的叙述和解释,所有原始仪式,都包括两个层面,即作为表演的行事层面和作为叙事的话语层面,动作先于语言,叙事源于仪式,叙事是用以叙述和说明仪式表演的,而关于宗教祭祀仪式的叙事,就是所谓神话。至于神,并非如以前的学者所相信的那样是古人出于无知和恐惧的凭空想象,而是由仪式中的祭司演变而来的,仪式的精神内涵凭借仪式主持者或表演者的肉身得以拟人化和具象化,这就是神的原型。另一方面,原始仪式的行事层面,在祛除了了巫术的魔力和宗教的庄严之后,就演变为戏剧,古希腊悲剧就是从旨在促进农作物增殖的春天庆典仪式(即所谓酒神节祭典)演变而来的。通过将神话和戏剧追溯到其原始仪式源头,哈里森对神和神话的起源、艺术和宗教的起源做出了极具新意的解释。受她的启发,当时剑桥的几位学者如穆雷(Gilbert Murray,1866—1957年)、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1874-1943年)等等对近东、希伯来、埃及、中世纪乃至“野蛮民族”的神话和宗教的仪式原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这就是学术史上有名的剑桥学派。尽管后来的学者对神话—仪式学说提出了种种批评和修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神话学家能够真正摆脱神话-仪式学派所奠定的学科基础及其提出的问题。
哈里森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平生游历八方,足迹几乎遍及欧洲所有古代文化遗址,涉猎古典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美学、神话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掌握了包括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语、俄语等在内的十六种语言,平生著述宏富,既有大部头的考据著作,如《希腊宗教导论》、《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再论希腊宗教》等,也有文字典雅流丽、颇具维多利亚时代散文风格的学术随笔,本书就属于后者。本书原为当时几位英国学者编辑的《现代学术•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种,由于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的知识大众,故作者在本书中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地对其关于古希腊宗教、仪式、庆典、神话、美术的见解做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使本书成为一般读者了解神话-仪式学说的最好的入门性和概论性读物,因此,出版以来多次再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因此,本书在引领读者深入古典学堂奥对古希腊文化寻根究底、追本溯源的同时,也用叙事化的笔调,向读者展现了古希腊多姿多彩、风情万种的宗教和风俗文化,尤其是她所刻意再现的古希腊春天庆典和酒神祭奠的狂欢光景,更令人情不自禁地流连低回、心向神往。
哈里森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波及整个世界人文学术界,余波所接,也影响了中国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20年代,周作人就曾著文介绍过她的学说,并翻译过她的著作,其《希腊神话之一》(见本书附录)一文,就是专门介绍哈里森关于希腊神话见解的。文章开头就提到这本《古代艺术和仪式》,并说自己和哈里森结缘,就是因为这本书:“我最初读到哈理孙的书是民国二年,英国的‘家庭大学丛书’中出了一本《古代艺术和仪式》(1913年),觉得它借了希腊戏曲说明艺术从仪式转变过来的情形非常有意思,……能够在沉闷的希腊神话及宗教学界上放进若干新鲜的空气,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这是我们非专门家所不得不感谢她的地方了。”如果不是因为战乱而导致的种种阴差阳错,以周作人著述之勤,以他在学术界的号召力,这本小书也许早就翻译成中文了。现在,哈里森的大部头论著《希腊宗教研究导论》(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1903年)和《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Themis: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Greek Religion,1912年)已经译为汉语,我们把这本小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读者,可以说是在重续文脉,完成一件前辈们早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工作。【2007年12月,北京】
下面是周二先生写的跋。
希腊神话一
哈理孙女士(Jane Ellen Harrison)生于—八五○年,现在该有八十四岁了,看她过了七十还开始学波斯文,还从俄文翻译两种书,那么可见向来是很康健的罢。我最初读到哈理孙的书是在民国二年,英国的家庭大学丛书中出了—本《古代艺术与仪式》(Ancient Art and Ritual,1913),觉得他借了希腊戏曲说明艺术从仪式转变过来的情形非常有意思,虽然末尾大讲些文学理论,仿佛有点儿鹘突,《希腊的原始文化》的著者罗士(R.T.Rose)对于她著作表示不满也是为此。但是这也正因为大胆的缘故,能够在沉闷的希腊神话及宗教学界上放进若干新鲜的空气,引起—般读者的兴趣,这是我们非专门家所不得不感谢她的地方了。
哈理孙是希腊宗教的专门学者,重要著作我所有的有这几部,《希腊宗教研究绪论》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1922三板)。《德米思》(Themis,1927二板),《希腊宗教研究结论》(Epilegomena,1921),其Alpha and Omega(或可译作《—与亥》乎?)一种未得,此外又有三册小书,大抵即根据上述诸书所编,更简要可诵。一为“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负债”丛书(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的第二十六编《神话》(Mythology,1914),虽只是百五十页的小册,却说的很得要领,因为他不讲故事,只解说诸神的起源及其变迁,是神话学而非神话集的性质,于了解神话上极有用处。二为“古今宗教”丛书中的《古代希腊的宗教》(Religion of Ancient Greece,1905),寥寥五六十页,分神话仪式秘法三节,很简练地说明希腊宗教的性质及其成分。三为《希腊罗马的神话》(Myths of Greece and Rome,1927),是彭恩六便士丛书之一,差不多是以上二书的集合,分十二小节,对于阿林坡思诸神加以解释,虽别无新意,但小册廉价易得,于读者亦不无便利。好的希腊神话集在英文中固然仓卒不容易找,好的希腊神话学更为难求,哈理孙的这些小书或者可以算是有用的入门书罢。
《希腊罗马的神话》引言上说:“希腊神话的研究长久受着两重严重的障害。其一,直至现世纪的起头,希腊神话大抵是依据罗马或亚力山大的中介而研究的。—直到很近的时代,大家总用了拉丁名字去叫那希腊诸神,如宙斯(Zeus)是约夫 (Jove),海拉(Hera)是由诺(Juno),坡塞同(Poseidon)是涅普条因(Neptune)之类。我们不想来打死老虎,这样的事现在已经不实行了。现在我们知道,约夫并不就是宙斯,虽然很是类似,密涅伐(Minerva)也并不就是雅典娜(Athena)。但是一个错误——因为更微妙所以也更危险的错误依然存留着。我们弃掉了拉丁名字,却仍旧把拉丁或亚力山大的性质去加在希腊诸神的上边,把他们做成后代造作华饰的文艺里的玩具似的神道。希腊的爱神不再叫作邱匹德(Cupid)了,但我们心里都没有能够去掉那带弓箭的淘气的胖小儿的印象,这种观念怕真会使得德斯比亚本地崇拜爱神的上古人听了出惊罢,因为在那里最古的爱洛斯(Eros,爱神)的像据说原来是一块未曾雕琢的粗石头呀。
“第二个障害是,直至近时希腊神话的研究总是被看作全然附属于希腊文学研究之下。要明白理解希腊作家——如诗人戏曲家以至哲学家的作品,若干的神话知识向来觉得是必要的。学者无沦怎么严密地应用了文法规则之后有时还不能不去查—下神话的典故。所以我们所有的并不是神话史,不是研究神话如何发生的书,却只是参考检查用的神话辞典。总而言之,神话不被当作—件他的本身值得研究的东西,不是人类精神历史的一部分,但只是附随的,是文学的侍女罢了。使什么东西居于这样附随的地位,这就阻止他不能发达,再也没有更有效的方法了。”
还有一层,研究希腊神话而不注意仪式一方面,也是向来的缺点。《神话》引言中说:“各种宗教都有两种分子,仪式与神话。第一是关于他的宗教上一个人之所作为,即他的仪式。其次是一个人之所思索及想像,即他的神话,或者如我们愿意这样叫,即他的神学。但是他的作为与思索却同样地因了他的感觉及欲求而形成的。”神话与仪式二者的意义往往互相发明,特别像希腊宗教里神话的转变很快,后来要推想他从前的意思和形守,非从更为保守的仪式中间友寻求难以得到线索,哈理孙的工作在这里颇有成就。她先从仪式去找出神话的原意,再回过来说明后来神话变迁之迹,很能使我们了解希腊神话的特色,这是很有益的一点。关于希腊神话的特别发达而且佳妙的原因,在《古代希腊的宗教》中很简明的说过:
“希腊的宗教的材料,在神学(案即神话)与仪式两部分,在发展的较古各时期上,大抵与别的民族的相同。我们在那里可以找到鬼魂精灵与自然神,祖先崇拜,家族宗教,部落宗教,神之人形化,神国之组织,个人宗教,魔术,祓除,祈祷,祭献,人类宗教的一切原质及其变化。希腊宗教的特色并不是材料,只在他的运用上。在希腊人中间宗教的想像与宗教的动作,虽然在他们行为上并非全无影响,却常发动成为人类活动的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此二者平常看作与宗教相远的,其实乃不然。这两种形式是艺术,文字的或造形的,与哲学。凭了艺术与哲学的作用,野蛮分子均被消除,因为愚昧丑恶与恐怖均因此净化了,宗教不但无力为恶,而且还有积极的为善的能力了。”(神话》第三章《论山母》中关于戈耳共(Gorgon)的—节很能具体的证明上边所说的话,其末段云:
“戈耳共用了眼光杀人,它看杀人,这实在是一种具体的恶眼(Evil Eye)。那分离的头便自然地帮助了神话的作者。分离的头,那仪式的面具,是一件事实。那么,那没有身子的可怕的头是那里来的呢?这—定是从什么怪物的身上切下来的,于是又必须有一个杀怪物的人。贝尔修斯(Perseus)便正好补这个缺。所可注意的是希腊不能在他们的神话中容忍戈耳共的那丑恶。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含愁的女人的面貌。照样,他们也不能容忍那地母的戈耳共形相。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
哈理孙写有—篇自传,当初登在《国民》杂志(The Nation)上,后又单行,名曰《学子生活之回忆》(Reminiscences of a Student's Life,1925)。末章讲到读书,说一生有三部书很受影响,一是亚列士多德的《伦理学》,二是柏格孙的《创造的进化》,三是茀洛伊特的《图腾与太步》(Totemism and Taboo),而《金枝》(The Golden Bough)前后的人类学考古学的书当然也很有关系,因为古典学者因此知道比较人类学在了解希腊拉丁的文化很有帮助了。“泰勒(Tylor)写过了也说过了,斯密斯(Robertson Smith)为异端而流放在外,已经看过东方的星星了,可是无用,我们古典学者的聋蛇还是塞住了我们的耳朵,闭上了我们的眼睛。但是一听到《金枝》这句咒浯的声音,眼上的鳞片便即落下了,我们听见,我们懂得了。随后伊文思(Arthur Evans)出发到他的新岛去,从它自己的迷宫里打电报来报告牛王(Minotauros)的消息,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件,这与荷马问题有关了。”
《回忆》中讲到所遇人物的地方有些也很有意思,第二章《坎不列治与伦敦》起首云:
“在坎不列治许多男女名流渐渐与我的生活接触起来了。女子的学院在那时是新鲜事情,有名的参观人常被领导来看我们,好像是名胜之一似的。屠格涅夫(Turgenev)来了,我被派去领他参观。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我敢请他说一两句俄文听听么?他的样子正像一只和善的老的雪白狮子。阿呀,他说的好流利的英文,这是一个重大的失望。后来拉斯金 (Ruskin)来了。我请他看我们的小图书馆。他看了神气似乎不很赞成。他严重地说道,青年女子所读的书都该用白牛皮纸装钉才是。我听了悚然,想到这些红的摩洛哥和西班牙皮装都是我所选定的。几个星期之后那个老骗子送他的全集来给我们,却全是用深蓝色的小牛皮装的!”末了记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后来在纽能学院所遇见的最末的—位名人即是日本的皇太子。假如你必须对了一个够做你的孙子的那样年青人行敬礼,那么这至少可以使你得点安慰,你如知道他自己相信是神。正是这个使我觉得很有趣。我看那皇太子非常地有意思。他是很安详,有—种平静安定之气,真是有点近于神圣。日本文是还保存着硬伊字音的少见的言语之一种。所有印度欧罗巴语里都已失掉这个音,除俄罗斯文外,虽然有一个俄国人告诉我,他曾听见一个伦敦买报的叫比卡迭利(Piccadilly)的第三音正是如此。那皇太子的御名承他说给我听有两三次,但是,可惜,我终于把它忘记了。”所谓日本的硬伊字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假如这是俄文里好像是Ы或亚拉伯数字六十一那样的字,则日本也似乎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学俄文的朋友读到这音也十分苦斗呷,——或者这所说乃是朝鲜语之传讹乎。
结论的未了说:“在一个人的回忆的末后似乎该当说几句话,表示对于死之来临是怎样感想。关于死的问题,在我年青的时候觉得个人的不死是万分当然的。单一想到死就使得我暴躁发急。我是那样执着于生存,我觉得敢去抗拒任何人或物,神,或魔鬼,或是运命她自己,来消灭我。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假如我想到死,这只看作生之否定,一个结局,—条末了的必要的弦罢了。我所怕的是病,即坏的错乱的生,不是怕的死,可是病呢,至现在为止,我总逃过了。我于个人的不死已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未来的生存也没有什么希求。我的意识很卑微地与我的身体同时开始,我也希望他很安静地与我的身体一同完了。
会当长夜眠,无复觉醒时。
“那么这里是别一个思想。我们现在知道在我们身内带着生命的种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生命,一是种族的生命,一是个人的生命。种族的生命维持种族的不死,个人的生命却要受死之诱惑,这种情形也是从头就如此的。单细胞动物确实是不死的,个人的复杂性却招到了死亡。那些未结婚的与无儿的都和种族的不死割断了关系,献身于个人的生活,——这是一条侧线,一条死胡同,却也确是一个高上的目的。因了什么奇迹我免避了结婚,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生都是在爱恋中的。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喜欢。我并不怀疑我是损失了许多,但我很相信得到的更多。结婚至少在女人方面要妨害两件事,这正使我觉得人生有光荣的,即交际与学问。我对于男子所要求的是朋友,并不是丈夫。家庭牛活不曾引动过我。这在我看去顶好也总不免有点狭隘与自私,顶坏是一个私地狱。妻与母的职务不是一件容易事,我的头里又满想着别的事情,那么一定非大失败不可。在别方面,我却有公共生活的天赋才能。我觉得这种生活是健全。文明,而且经济地正当。我喜欢宽阔地却也稍朴素地住在大屋子里,有宽大的地面与安静的图书馆。我喜欢在清早醒来觉得有一个大而静的花园围绕着。这些东西在私人的家庭里现已或者即将不可能了,在公共生活里却是正当而且是很好的。假如我从前很富有,我想设立妇女的—个学问团体,该有献身学术的誓言和美好的规律与习惯,但在现在情形之下,我在一个学院里过上多年的生活也就觉得满足了。我想文化前进的时候家庭生活如不至于废灭,至少也将大大的改变收缩了罢。
“老年是,请你相信我,一件好而愉快的事情。这是真的,你被轻轻地挤下了戏台,但那时你却可以在前排得到一个很好的坐位去做看客,而且假如你已经好好地演过了你的戏,那么你也就很愿意坐下来看看了。一切生活都变成没有以前那么紧张,却更柔软更温暖了。你可以得到种种舒服的,身体上的小小自由,你可以打着瞌睡听干燥的讲演,倦了可以早点去睡觉。少年人对你都表示一种尊敬,这你知道实在是不敢当的。各人都愿意来帮助你,似乎全世界都伸出一只好意的保护的手来。你老了的时候生活并没有停住,他只发生一种很妙的变化罢了。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光亮,不过你恋的那么温和就是了。在老年时代你简直可以对男子表示你喜欢和他在一起而不致使他想要娶你,或足使他猜想你是想要嫁他。”
这末了几节文章我平常读了很喜欢,现在趁便就多抄了些,只是译文很不惬意,但也是无法,请读者看其大意可也。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于北平。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