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放下手中的急活儿,仔细读了一本书:《寻找香格里拉》(沈卫荣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据书前扉页上介绍:
“沈卫荣,1962年生于江苏无锡,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1998年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获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系合作研究员、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代理教授、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合作研究员等。主要从事西域语文、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比较研究。”
“《寻找香格里拉》所录系作者对国学、‘西藏问题’和学术方法等热点问题的思考,发表以来深受学界和文化界好评。作者的‘大国学’理念别具一格,对‘语文学’的阐释和倡导发人深思。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经历,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使作者对国际视野中的“西藏问题”有非常透彻和独到的见解。通过对一个西方后现代的乌托邦神话——‘虚拟的西藏’(即香格里拉)的解构,作者为世人理解西藏、西藏文化和所谓‘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之所以读这本书,纯粹是因为偶然读到作家马丽华为该书所写的序言。在序言中,马丽华对沈卫荣其人、其书有着高度的评价。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点都不了解沈卫荣教授,对于他所研究的西域文史和藏学、佛学领域更是心怀敬畏。这本书可称作是学术散论集,书中虽有沈教授个人的求学与治学经历,更多的则是对西方藏学、汉学研究的辨析与反思,尤其是对西方“虚拟的西藏”(即香格里拉)的解构,读来十分过瘾。
沈教授的文字平实,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不急不躁的学理论辩,寓尖锐锋芒于绵软花丛之中,每篇文章虽是各自独立的篇章,但读来不忍释卷,不知不觉就从序言读到了后记。好久没有这样一页一页、一字一字的读书了!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和《我的心在哪里?》两篇文章。
读罢上述两篇文章,我才真正弄明白了当年傅斯年先生为什么要在中央研究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和“语言”为什么能够凑到一起;才知道了西方“语文学”的传统对我国现代学术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沈教授从西方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又谈到了中国传统治学的“理学”和“朴学”之争。沈教授在《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的文末有句发问:不知今天是不是又到了“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时候了?此问当问!
读着沈教授的文字,想到了学弟施爱东近来正在做的事情:在日本东大图书馆钻故纸堆,追溯考证拿破仑的“醒狮论”、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龙”的形象。爱东向以辩才著称,给人以“理学”传统的感觉,但他最近即将出版的《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以及上述考证“醒狮论”、“中国龙”的文章,则充分显示出中国“朴学”的传统。考证与义理在今日治学是不可分的,但我们民俗学的研究,现在虽然理论尚有不足,但更需要提倡的,则是扎扎实实地对浩如烟海的民俗材料进行记录、辨析、归纳和解释,在言之有物的调研、爬梳的基础上,总结出符合中国民俗发展规律的理论。
3月7日 凌晨
《寻找香格里拉》目录
初识冯其庸先生
闲话国学与西域研究
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
我的心在哪里?
说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
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佛教研究
大喜乐崇拜和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
《欲经》:从世间的男女喜乐到出世的精神解放
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说跨文化误读
谁是达赖喇嘛?
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我读马丽华
“汉藏佛学研究丛书”编辑缘起
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
写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出版之际
后记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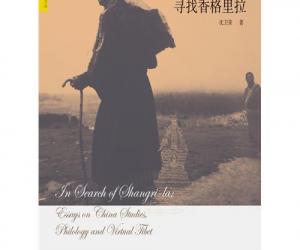 书影《寻找香格里拉》
书影《寻找香格里拉》 [时间:2011-3-7 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