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和
《 光明日报 》( 2013年01月13日 05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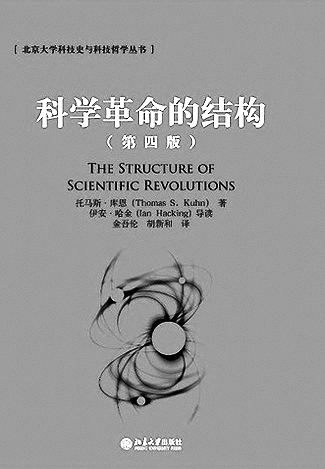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版
[美]托马斯·库恩 著 金吾伦、胡新和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一书出版50周年。库恩的这本书或许是当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界中影响最大的一书,其影响早已超出了这个圈子,甚至扩散至学术界之外的诸多领域。从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英语版《结构》的总销量已达到140万本。若再算上其他26种语言的译本,其数量当属惊人。以时下最时兴的评价标准——被引用率来计,《结构》也是所有出版物中被引用率最高的书籍之一,其排名直逼西方经典的《圣经》和弗洛伊德的著作。至于作为其核心概念的“范式”及“范式转换”的通俗流行,已经到了化身为时尚的程度。早在1974年,《纽约人》杂志就曾刊登过一幅漫画,嘲笑“范式”被滥用的现象:在曼哈顿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位体态丰腴、身着喇叭裤的女士对一位自诩时尚的谢顶男士说:“Gerston先生,您可真是语出惊人!之前我还从没听过有人会在现实生活中用上‘范式’这个字眼。”而在此后的1995年、2001年和2009年,该杂志还陆续刊出过类似的漫画。
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为什么会有如此范围广泛的传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缘由很多。首先,话题吸引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正当走红之时,讨论其历史发展变革,给出一个易于理解把握的框架,这一选题不仅有学术价值,也符合大众传播和公众心理需求;其次,在于库恩运用词语的天赋,加拿大学者伊安·哈金称之为“点石成金”。在库恩的手里,常规科学——解谜——范式——反常——危机——革命,再加上不可通约性和世界观的转变这一系列来源各异,但大体上通俗(除了“范式”一词以外)的术语组合起来,构成了一套看待科学世界及其历史演化的“格式塔”;当然最为关键的是,由于库恩的这一框架有他多年历史研究的支撑,具备相当的解释力,并且不乏推广到其他学术领域以解释相似的理论更替现象的可能,因此,库恩及其“范式”学说的爆红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回到库恩自己感兴趣的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科学哲学领域。库恩学说的特点,首先是其历史性。基于历史事实,采用历史视角,运用历史方法(案例研究),说明历史现象,这正是库恩学说的出发点。也唯其如此,他与传统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走向形成对立,倡导了一种研究方法和路向的转折——“历史的科学哲学”,构成了一种所谓历史主义的应然。库恩因此成为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转向的标志性人物,使得历史、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成为理论发展和选择中不可回避的因素。
库恩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其革命性。这里似乎再一次体现了某种自返性。如果说是研究历史的实然返回来使库恩自身成为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模型的提倡者,那么,也正是研究历史上的科学革命,研究革命前后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使库恩自身完成了科学哲学中的革命,至少库恩自己体验到了这种心理过程的革命性变化——格式塔转换。“发现了历史,也发现了我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后寻求最好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成了寻求另一次这样的革命事件。要认识并理解这些事件,只有对过时的文本恢复过时的读法。”(范岱年等译《必要的张力》)“革命”一词当然来自政治领域,库恩借喻于此,是想来表明新旧两种理论范式转换所带来的那种变化,是天翻地覆式的震撼,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世界观的转换,这种变化是彻底的,不连续的,不可通约的,这就不仅颠覆了传统科学发展的累积主义观念,更打破了新旧理论的发展是朝向一个目标(真理)不断逼近的连续演进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所强调的这种新旧理论之间真值不连续性的革命性,可以比之于普朗克量子假说中的能量不连续性的革命性,由此所引爆的争议自然也就是可以预期的了。
库恩学说的历史性,当然会招致逻辑经验主义者们的批评非议,而他的不可通约性所蕴含的理论真值的不连续性或不可传递性(新的理论并非必然包含旧理论作为自身的特例),也恰恰是他用“革命”一词的本意,却使他经受了来自各方,包括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者的责难,这使他极为苦恼。一方面,不可通约性的观念是他的历史研究的逻辑必然,是他全部学说的根基所在,他自然不会放弃,从《结构》发表到1996年去世前的30多年中,他都在致力于捍卫这一思想;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抱着哲学意图来研究历史的物理学家”,库恩不仅不会全然放弃“真理”这样的概念,而且还想用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词意义和逻辑分析的工具,来表达自己的革命性观念,由此造成的“人格分裂”则成为其学说的另一特征——二象性(duality)悖谬。这种悖谬表现在作为一位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库恩后期致力于用逻辑经验主义所习用的论证方式和工具来为自己学说的合法性作辩护;作为一位革命性的标志性人物,库恩也十分烦恼科学知识社会学者们对他思想的曲解或误解,把他的思想推向极端。
事实上,我们在此可以借喻库恩对于哥白尼的二象性形象的解释:“尽管历史学家偶尔会为了哥白尼究竟是最后一个古代天文学家还是第一个近代天文学家争得面红耳赤,然而这种争论从根本上是荒谬的。哥白尼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近代的,而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两种传统在他的工作中融合在一起。追问他的工作究竟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就如同追问一条别处都是直的道路的转弯处是属于转弯之前的那段路还是属于之后的那段。在转弯处,道路的前后两段都可以看到,而且其连续性十分明显。可是从转弯之前的位置看去,道路似乎直通向转弯处然后就消失了,转弯似乎是直道的最后一点。而从转弯之后的另一段路上某一点看来,道路似乎是从转弯处开始一直下来。转弯处同等地属于两段路,两段都不属于。它在道路前进的方向上标记出一个转折点,就像《天体运行论》在天文学思想的发展中标志着一次转向一样。”(吴国盛等译《哥白尼革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所谓革命性的人物都具有这种传统与革命的二象性:他来自传统,必然带有传统的思想痕迹,从转弯之前的位置看过去,可以看到他的背影;他率先转折,面向新程,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这些革命性人物背负的传统和转折的彻底会因人而异,但这种“二象性”的色彩则在所难免,当年的哥白尼如此,普朗克如此,库恩本人也难逃此律。但这无损于这些思想家的重要性:毕竟是他们,为我们开拓出了历史和思想演变的新的路径。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