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 征文选登
个人口述的意义
■冯磊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2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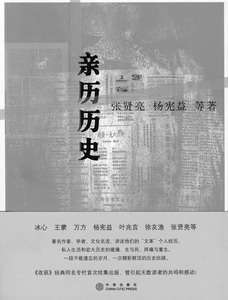
中国的历史,严格来讲都是帝王的家史。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修订历史。这其中,固然有些许是为了文化的传承,更多的,则恐怕是为了达到粉饰自己的目的。一部《二十五史》,其中究竟有多少东西是真实的,有多少东西是扭曲的甚至颠倒黑白的。作为后来者,我们不得而知。
与正史相对应的,民间修史也是一种传统。但是,因为存活的不易,这类资料保留下来的比较少。于是,一些个人笔记、日记、随笔甚至回忆录就成为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很多时候,研究者宁愿相信个人的笔记和日记,也不愿意相信正史。这是有道理的。相对于被权力屡屡染指的所谓正史,民间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可能更高。至少,正史与民间史料可以起到相互照应、彼此参考的价值。
《收获》杂志搞了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栏目——“亲历历史”。顾名思义,这个栏目所搜集的,都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于往事的回忆。其中的只言片语,在今天看来已经弥足珍贵。这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关于往事的记忆已经日渐模糊。当更多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当代历史中的一些事件和人物,还原的难度将越来越大。而《收获》所做的工作,固然是应该进行的工作之万分之一,却实在因为创意的价值,而成为功德无量的一件事。
日前,中信出版社以《亲历历史》为书名,结集出版了《收获》杂志所刊登的部分文字。在书里,有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有叶兆言的“文革”记忆,有徐友渔讲述的大串联,有冰心老人写给家人的书信……在书里,“文化大革命”不再那样遥远,往事的一幕幕都细节化和具体化了。这些作者以亲身见证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文革”,一段被称之为“浩劫”的历史。
翻读这本书,最打动我的莫过于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在解放前就坐牢,文革中仍然坐牢的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在监狱里,他赢得了犯人的普遍尊重。犯人们私下里说,“他和咱们不是一样的人”。这位老人在监狱里,平日里不卑不亢,很少言语。但是有一天,他开口说话了。老者说道:“在成功之外,至少还有两件可以使得人生具有意义的事:一是忍受苦难,一是沉思默想。”——这对于能够在书桌边静静思考,或者整天无所事事的人而言,确实是一种震撼。
张贤亮曾仔细研读《资本论》,他写道:“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这段话,很值得玩味。——被屡屡揪斗的大“右派”,面临继续的监狱生活,竟然是窃喜。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可是当一个“思想犯人”的身份被确定、被打上标记,他在自由天地的生活就得时刻小心翼翼。这样的生活,远不如在农场里劳动、和一群劳改犯朝夕相处来得快乐。
张贤亮的快乐,究竟是人类随遇而安的天性,还是某种处世的狡猾,抑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版本再现?我觉得,值得仔细思考。当一个人安于被关押的和没有尊严的生活,他对外面的天空已经失去了兴趣。这,确实让人感到震惊。
铭记历史,记住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不堪入目的一面,对于告诫未来、防止悲剧重演都有重大的意义。从此而言,“文革”这段历史固然让人伤感,却具有使我们民族保持清醒的价值。
“文革”,是一味药。已经过世的巴金老人,曾经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但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这个心愿并没有变为现实。今天,当我们捧读《亲历历史》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一座文字的博物馆已经建造起来。这座博物馆,也许比实体的博物馆更具价值。
《亲历历史》,张贤亮、杨宪益等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28.00元